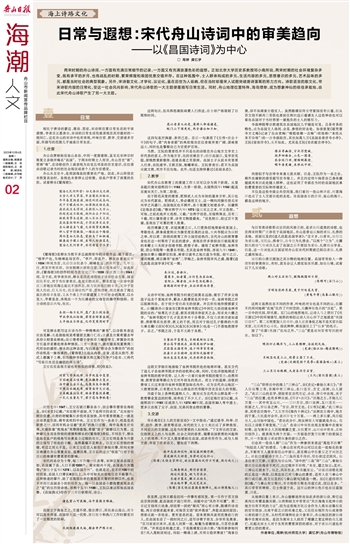□ 周婷 龚忆梦
两宋时期的舟山诗词,一方面有充满日常细节的记录,一方面又有充满浪漫色彩的遐想。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所说,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繁荣辉煌和艰困忧患交错并存。在这种氛围中,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另外,宋诗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虽在后世为人诟病,但在当时却是宋人试图突破唐诗藩篱的努力方向。诗歌语言的散文化,带来诗歌内容的日常化,受这一社会风尚影响,宋代舟山诗歌的一大主题便是描写日常生活。同时,舟山地理位置特殊,海岛缥缈,成为想象神仙的极佳承载地,由此宋代舟山诗歌产生了另一大主题。
壹 日常
相比于唐诗的豪迈、激动、悲凉,宋诗则注重日常生活的平淡感情。学者吕正惠表示,宋诗的日常生活性就表现在其对题材的一视同仁。这在舟山的宋诗中也有体现,吟咏仕宦、教学、交游诸多方面,所描写的范围几乎涵盖日常生活。
1.仕宦
舟山自唐朝始设翁山县治,中间一度废建制,直至北宋神宗时期复立县制并赐名“昌国”。于两宋时期士人而言,舟山历史“新”、管理“难”,在诗歌创作上就表现为自觉且明显的历史意识,往往借由诗歌记录当时的社会现状或者个人的为官感受。
舟山从古至今,是我国海盐的重要出产地。因此,舟山即使在未恢复县治时,盐税也未曾停止过收缴,给盐户带来了深重的负担。试看柳永《鬻海歌》:
鬻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
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鬻就汝输征。
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
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
卤浓咸淡未得闲,采樵深入无穷山。
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
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
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
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
秤入官中得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
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鬻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
《鬻海歌》是柳永为数不多且流传至今的诗歌作品,题下原注:“悯亭户也,为晓峰盐场官作。”亭户,即盐户。柳永自景祐元年(1034)释褐为官,先后任余杭县令、晓峰盐监、泗州判官。九年三任,所至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最后竟未成行。据此推测,《鬻海歌》的创作时间当在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间。鉴于此,有学者推测,柳永是因此诗得祸才导致仕途失意。国泰但民不安,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柳永在这一首诗中屡次三番地强调海边盐民不得休息,极力渲染他们的辛苦,无异于在揭人伤疤、打人耳光。但全诗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既反映出了海边盐民的艰辛生活,又从个体上升到家庭复上升到社会的高度,以小见大、卒章显志,体现出一个为民请命的父母官的操守和信仰。在全诗的最后六句,他说:
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
甲兵净洗征输辍,君有余财罢盐铁。
太平相业尔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
可见柳永把写这首诗当作一种特殊的“谏书”,以诗歌来表达政治见解:先是描绘现实希望君主施行仁政;次谈及政策希望去甲兵存余财罢盐铁税;最后寄希望于宰相尽力辅佐帝王、审慎协调各方权益并妥善处理各种情况。三方一齐用力,就有望实现夏商周三代而治的盛世。柳永的这种态度,与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动机是一脉相承的。《鬻海歌》无论从内容、主旨,还是从技巧、形式上都属于上乘,引得钱仲书称誉其和王冕《伤亭户》是宋、元两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
王安石在盐税方面也有相似的诗歌,即《收盐》: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郗,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就任鄞县县令,因公事所需曾出海收盐。据《宋史》记载:“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北宋初年财政空虚,政府的财赋集权步伐明显加快,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推动茶盐引法,将专卖收归中央。王安石作为一县县令,收盐是其职责之一,因而有机会目睹“吏兵”的执行过程。海中岛夷生计艰难,只能依靠“煎海水”来维持温饱,希望“君子”能够以民为重。这种睹民生而生怜悯的感情和柳永的《鬻海歌》类似。不同在于,柳永是站在盐户的视角写出煮盐全过程的艰苦,王安石则是身为州家的立场写了收盐的辛酸。虽然篇幅不及柳永,但王安石悲悯的情绪,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王安石在入朝担任参知政事,即向宋神宗奏请在舟山重置县治。追溯因果,王安石的这次“收盐”行对于他日后的奏请有着重要的影响。
宋代的县分为十等,每三年升降一次县等。宋神宗复县昌国之初,昌国属下县,人口不满1000户。南宋绍兴年间,昌国县升为望等;“至元十五年(1278),以昌国升州”。也就是说,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昌国人口增长8倍以上,从中可知其政治地位在不断攀升。这样快速的攀升,除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及政策的扶持以外,也离不开历任昌国县令的积极作为。每一任昌国县令都抱着实现县名之“意”的强烈使命感。淳熙十五年(1188),王阮以承议郎知昌国县事。《昌国偶成》即作于三年任职期间,诗云:
诸邑皆山可夜驰,海中昌国力难施。
昌国立于海岛之上,交通不便,信息滞后,其他县山连山,政令可以连夜传递,昌国却无这一优势,推行政令和执行工作时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风潮阻渡连天地,期会申严限日时。
这两句说,狂风和怒潮阻碍着人们传达,政令却严格限制了日期和时间。
愿以老身从此免,漫将人命逼诸危。
蛟门山下须臾死,肉食诸公知不知。
这四句直抒胸臆、表明己志。最后一句袭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句子,借“肉食者鄙”的典故规劝在位者眼界要广阔、谋略要远大,同时也是警醒自己为官爱护百姓。
当然,王阮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他的诗歌在舟山地方文学史上所代表的意义。作为地方官,他的贡献在于:到任昌国后,见学宫芜隘,便慨然重新整修,徙建县南之芙蓉洲。昌国士子从前未有登第入仕者,自阮建学,文教丕振,魁辅辈出。王阮曾表示:若不为昌国成就文教,死亦不往他地。此外,他还主持修纂过《昌国县志》。
2.教学
宋代舟山在教育上的重建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复县起到南宋绍熙四年(1193),为第一阶段。从绍熙四年(1193)起直至南宋灭亡,为第二阶段。
出于防范兵变的需要,贬抑武人成为宋初的基本方针,其后也成为宋代家法。贬抑武人,势必擢用文士,这一倾向间接致使北宋兴学之风盛行,昌国地区也不例外,县令张懿文初建县学。据康熙《定海县志》载:“惟宋熙宁六年(1073)迨元至正之末,皆立邑校。”可知,之前此地并无邑校。又载:“自熙宁创邑,至绍熙癸丑,百有二十载,而应傃登进士第,诗书文物浸盛矣。”设邑校后,经过百年发展,显现出了可喜的育人效果。
经历靖康之变、衣冠南渡之后,人们更热切地期盼收复国土,考取功名、跻身庙堂则成为接受度最高的途径,大兴书院成为应时之举。所以第二阶段的教育工作全国空前热烈。古代舟山的教育事业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许多曾经出任朝廷高官的本籍士大夫回乡创建书院、教授子弟。涌现了虹桥书院、翁洲书院、岱山书院等一批著名书院。尤其是翁洲书院。淳祐九年(1249),参知政事应亻繇辞官归里,将昔日读书之地改造为书院。经年之后,遂成规模,理宗御书“翁洲”二字赐之。翁洲书院学风之盛,陈著《送儿沆赴昌国学录》可见一斑:
来汝沆,吾语汝:
蓬莱乡,仙者寓,汝行岂为求仙故。
宝陀山,佛者住,汝今岂为礼佛去。
吾闻滃洲好学舍,兵后弦歌尚存鲁。
从诗中可知,翁洲书院当时就已经美名远扬,吸引了许多父母送子远去千里地求学,鄞县人陈著便是其中的一员。翁洲书院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较少受到兵戈的侵袭,并且积极地传授儒家文化。应亻繇族孙应奎翁在《重修翁洲书院记》中回忆先祖创建翁洲书院的目的:“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闻清净寂灭之念,而求夫六籍之学。”翁洲书院对于孔子及其学术十分尊崇,不仅力求肃清诸如道教、佛教等其他思想、教义的干扰,而且对于经过孔子整理的六部先秦古籍(《诗》《书》《礼》《易》《乐》《春秋》)也是一门不落地教授学子。总之,“书院之设,于是不无助于圣教。”
巨鳌拄牢苍壁岛,长鲸截断红尘路。
黄公高节懔犹在,茹侯英标俨如睹。
芷翁器业国有传,逸少词章家有谱。
扶桑日出长精神,沧溟际天豁襟宇。
潮水生落见乘除,风涛澎湃尝敛阻。
这段文字细致地描绘了翁洲书院所处的地理环境,甚至交代了送儿子去翁洲书院求学的动机和心理。同时,它也详细地阐述了翁洲书院的教学优势。让人再一次看到翁洲书院的吸引力:自然环境、教育资源等都成为它对外招生的亮点。而士子的追捧、诗歌的赞颂又反过来使得翁洲书院更加驰名中外,成为古代舟山地区一大教育招牌,后来更成为舟山群岛历代书院中历史最长久的书院。
得益于如上各种机遇和人力,南宋成为古代舟山群岛第一个教育事业发达的时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据《定海厅志》记载,从绍熙四年(1193)至咸淳九年(1273)80年间,昌国有33人考中进士,更多次出现了父子、叔侄、兄弟同登金榜的喜事。
3.交游
邓小南在《士人的交游活动》一文中指出:“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下文所说的交游,仅指狭义上的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游赏。随着昌国教育的兴起和人才的培养,不少文人墨客都前往昌国,或欲有所作为,或与人相交游,并留下许多诗文。譬如底下两例:
欲冲高浪却沉吟,酒近瀛洲懒得斟。
莫道颠风无好意,为君吹过远归心。
(陈瓘《文饶自京师还,欲往昌国而风作不可渡,绝句戏之》)
已闻舟楫具,那得苦留君。
雨过风霜急,帆飞雪浪分。
长途方策足,暇日正论文。
功业他年事,风波岂足云。
(陈瓘《苏文饶往昌国意颇惮之,送以诗因勉之》)
很显然,这两首都是因同一件事有感而发。第一首作于苏文饶自京师回程、赴昌国前夕送行所作。诗题中说“风作不可渡”。第二首记文饶再次动身,却因第一回的“颠风”而心有余悸,陈瓘作诗劝勉。两首诗联系起来看,可知苏文饶“欲冲高浪”、奔赴昌国的原因:想要成就一番功业。更有意思的是,原本畏惧风波而犹豫前行的人,在昌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还写诗寄予朋友、分享所见美景,“百川衮衮到来休,此是人间第一流。鲸鬣为君翻骇浪,兰苕空自满汀洲。”并表达出相邀之意。于是陈瓘复以诗次韵:“海邦渺渺知何在?风入高帆顷刻过。何似一樽湖上酒,月明安稳照寒波?”海景壮美,却不如湖景安稳宜人。虽然陈瓘最终安守家园没有应邀,但从苏文饶不顾再三受阻也要前往和到达后邀请友人这些举动也可以看出昌国对于当时想要一展抱负的士人的吸引力。
寺庙禅院等宗教建筑在昌国地区几乎随处可见,且各有各的特色,成为昌国文人消闲、会见、参悟的好去处。如晏敦复《题梵慧寺方丈梅》记录了他由赏梅(“桠槛欹檐一古梅”)而悟理(“本性从来不染埃”)的一次寺庙经历。其他如高九万《昌国县普济寺小亭》、王阮《宿祖印寺》,无不如此。尤其是王阮《劝农题吉祥寺》:
傍石寻幽径,穷源得梵城。
潮声四面合,山色一团清。
农合巡门劝,僧烦倒屣迎。
明年吾更健,来伴此中耕。
内容似乎与吉祥寺本身无甚关联。但是,王阮作为一县之长,将外出履职的感受题写在寺墙上,并且约定明年倘若自己身体康健就再来到此处随人耕种,这也证明了寺庙在当时的昌国地区承担着重要的交际和传播意义。
不仅是这些寺庙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山林泽薮、村落海岸也成了士人交游独处的去处。像昌国县东的泄潭、翁山的海岸,都是这样的地方。
贰 遐想
与日常类诗歌形成强烈的风格差的,是求仙问道类的诗歌,也在两宋时期广泛存在于昌国地区。舟山是普遍认知的求仙、礼佛的圣地。前面提及的《送儿沆赴昌国学录》:“蓬莱乡,仙者寓,汝行岂为求仙故。宝陀山,佛者住,汝今岂为礼佛去。”以两个“岂为”、充满担忧的语气告诫孩儿去了昌国之后不要因为求仙、礼佛耽误学业。但是,这一告诫也从反面证明舟山在宋代时期就已经以求仙、礼佛之盛而知名。
浓厚的仙佛氛围加之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昌国常常给人一种缥缈的审美体验。有时,甚至会让人感觉如至桃源、如临仙境。试看以下几首诗歌:
两山对立石为门,疑隔桃园旧日村。
(陈明可《石门山》)
万顷沧浪终月夜,更于何处觅天宫。
(黄龟年等《马秦山联句》)
这两首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吟咏的对象也是不同的山,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此地”比作了跨时空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彼处”。第一首中的桃园,即桃源。石门山的地形地貌,让诗人马上想到了《桃花源记》中的环境描写,地形的相似让诗人疑心脚下之地就是“桃园旧日村”。第二首则更加大胆奇妙,诗人放言身处之地不是天宫胜似天宫,无须再费心寻找。经此种种,将昌国镀上了“仙乡”的色彩。
除了“桃源(桃园)”比喻之外,“三山”更是被频繁书写到的对象。如以下:
明朝归去鹤齐飞,三山乘缥缈,海运到天池。
(史浩《临江仙·题道隆观》)
片帆落处是三山,绝景尘居了不关。
(史浩《次韵范经干昆季<昌国杂咏>》其三)
三山月淡白银阙,九老春闲紫石宫。
(王阮《留别昌国》其三)
“三山”即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此后三山的名字,便经常在古代笔记、小说、传奇中出现。关于“三山”的位置,也有多种说法。《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中有五山焉,……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方壶,即方丈也。《汉书》记载:“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又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瀛洲在东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洲上多仙家,风俗似吴人,山川如中国也。”若据此分析,则瀛洲极大可能就是舟山。爬梳以上诗歌不难发现,“三山”在诗词中频繁出现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这与南宋士人历经靖康之变、皇权更替、山河破碎有关,反映到创作上,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抒发雪耻情节的爱国之作,另一方面是寻求避世保身的游仙之作。
但也有一些诗人将“三山”作为一种参照来表达“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的感受。马秦山在宋代舟山可以说是一处知名的景点,不断有文人墨客前往山中游玩,甚至将山中胜景呈之于画图之上。胡长孺曾题诗于图上:“三岛得见不得到,引船欲过遭回风。仙圣往来岂荒渺,吾意只与兹山同。”诗中的“三岛”即“三山”。秦始皇曾派徐福出海求不死药,但过程并不顺利,“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胡长孺诗歌化用的正是这一典故,以表达自己对马秦山的喜爱。还有人在马秦山中修行或隐居,前文提及的《马秦山联句》就是一例。据《乾道四明图经》载:“马秦山有安期洞,耆老相传安期生得道隐此,因以名乡。”其后常常有禅师、隐士修道于此,这座山的神仙色彩也被日益加重、固化。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舟山能够流传出如此多的游仙诗,和它远离内陆有着直接关联。仙传和经文中常常说“天涯海角某处神奇的地方拥有不死的力量”,因为这些地方既适合作为人类躲避集权化的官僚统治、逃离平原之后的藏身之处,又往往被视作为仙或者修仙者的居住之所。从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来讲,舟山地区的游仙诗集中在南宋出现,是因为南宋士人经历了靖康之变这样的战乱流亡,比起北宋士人对于生死有着更深切的感触、对于求仙问道也有着更迫切的需求。
作者单位:周婷(杭州师范大学) 龚忆梦(舟山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