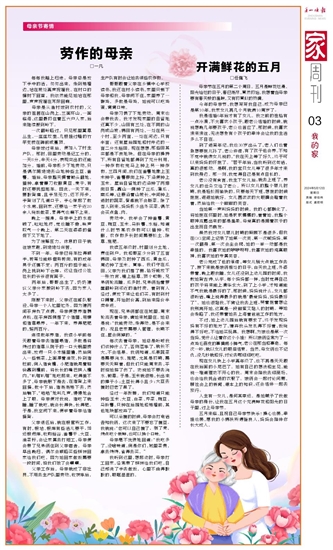□一凡
每每我踏上归途,母亲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匆匆出来,走到矮墙边,站在坡处高声祝福我。在村口的樟树下回首,我依然能见她站在那里,声声祝福在耳际回响。
母亲是从渔村嫁到农村的,父亲的祖居在山岗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这里最初住着五六户人家,后来陆续搬到岭下。
一次翻岭路过,只见那里蒿草丛生,一座座坟茔,几根挂过幡的竹竿支棱在碑前或墓顶。
母亲嫁过来后,便加入了村生产队。那时,田里劳动是记工分的,一天8分,半天4分,表现突出的还能加分。婚前,母亲极少下地劳动,只是偶尔随姥姥去山地种些土豆、番薯。婚后,母亲整天摸着锄头翻地、播种,拿着镰刀收割黄豆、麦子,有时还要挑担拖车。因此,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且手足无力,迈不开步,手背划了几道口子,手心燎起了数个水疱,回到家,还要给一家子近20余人烧饭做菜,累得气也喘不上来。
晚上一搓澡,母亲手上的水泡破了,咝咝地疼,觉也睡不稳,唉声叹气一个晚上,第二天在婆婆的催促下又下地了。
为了缓解压力,休息的日子就往娘家跑,到姥姥处诉苦。
不到一年,母亲已将车拉得顺手,转弯处能够借势转向,有的成年男子还搞不定;两百斤的担子能从岗上挑到岭下仓库,这让当过公社社长的爷爷很有面子。
两年后,哥哥出生了,奶奶建议父亲分家搬到岭下去,因为家人太多了。
刚搬下来时,父亲还在部队服役,母亲一个人忙里忙外。因为建两间平房负了点债,母亲便想养猪攒点钱,在平房西侧搭了个猪圈,用糠和猪草喂养,一年下来,养得肥肥的,超两百斤。
连续数年养猪,我读小学前每天跟着母亲去猪圈喂猪,多数是将烤过的猪草从院子的一口大锅里捞出来,放进一只小木桶里撸,然后倒入一些剩菜,上面漂着油花,拎到猪栏前,倒入猪食槽。小肥猪就晃着脑袋靠到槽前,将长长的嘴巴拱入槽内,“叭嗒叭嗒”地吃起来。吃得差不多了,母亲就躬下身去,在猪背上来回搔,数十下后,猪渐渐矮下去,然后躺下,“咕咕”地叫几声,慢慢地合上了眼。母亲便对我说,猪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就会长得快,长得肥。于是,我空闲下来,便学着母亲给猪搔背。
父亲退伍后,就在粮管所工作,有时,粮站、粮库有些活儿要干,如运粮进库,收购稻谷、番薯干、大豆、油菜籽,会让家属去打短工,母亲便会带了兄弟俩住到父亲宿舍。母亲早出晚归,偶尔会顺路买些糕饼回家给我们吃,因为她回家做饭需要一段时间,怕我们饿了会嚷嚷。
父亲工作后,母亲就成了非社员,不用去生产队里劳动,收获季后,生产队有时会让她去领些农作物。
哥哥跟着父亲在乡镇中心学校读书,我还在村小读书,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母亲闲不住,家里养了一群鸡,多数是母鸡,她说可以吃鸡蛋,调调口味。
母亲习惯了下地劳动,周末也会带我去,我才发现家里的自留地还真不少,山田有三处,在不同的山岗或山坡;棉田有两处,一处在另一个村,至少两亩,一处在河边,只有半亩;还有屋后园地和村井边的一亩二分水稻田。现在想想,那些田其实都是不良地块,但在母亲的操持下,所有自留地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一种作物收完马上种上另一种作物。三四月间,我们在番薯地撒上玉米种子,番薯藤向上捋,下沿便种上玉米。屋后自留地的边沿种了两排向日葵,靠山一侧种了丝瓜、蒲瓜、南瓜等,让藤沿着山坡长,中间种上适时的蔬菜,餐桌就不会断菜。除了客人到来,妈妈极少出外买菜,偶尔会买点鱼、肉。
劳动中,我学会了种番薯、黄豆、豌豆、玉米、马铃薯、水稻,知道什么时节某农作物可以播种、收割,农作物多长时间需要松土、除草、施肥。
我读五年级时,村里划分土地,责任到户,我和哥至少分到了五亩棉田,母亲及时种了西瓜、黄金瓜,周边种了玉米。夏季,我们守在瓜田,父亲为我们搭了棚,恰好能放下一张竹床,铺上稻草,顶个蚊帐,兄弟俩轮流睡。瓜多时,兄弟俩抬着箩筐翻岭到邻近的渔村卖,看到有人经过,便放下来让他们买,有时到村口蹲着,开始时价高,到后来降价半卖半送。
现在,兄弟俩都住在城里,周末轮流去看母亲,请她来城里住。她总是说:“我能劳动,走得动,是不会来的;况且老家需要人管理,长期不住,屋会倒掉的。”
每次去看母亲,她总是吩咐我们该种什么了,否则落季了,就长不大,不会结果。我俩知道,瓜果蔬菜是需要浇水、施肥,尤其是初期,需要天天照看,但我们只能周末去,平时怕她摔了伤了,劝说她不要去浇水、锄草。于是,玉米就很矮,长出来的棒子小;土豆长得小且少;大豆去摘时已老了黑了。
经过一年折腾,我们知道只能种些玉米、大豆、白菜、芹菜、豌豆、马铃薯,只种在后园地和矮墙前,其他地块都放弃了。
可以采摘的时候,母亲会打电话告知我俩,这次来了不要忘了摘豆。我就说:“您可以自己摘了,剥了壳,烤点吃个新鲜,也可以换个口味。”
母亲毫不犹豫地回道:“我吃多了,没啥味道,倒是你们,城里菜贵,拿去烤烤,省得去买。”
我听到这里,想起幼时,母亲打工回家,经常带了糕饼给我们吃,自己却洗了手去做饭,心里不由得酸酸的,眼眶湿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