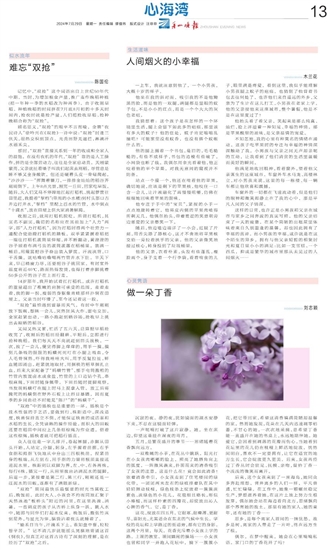陈国伦
记忆中,“双抢”这个词语出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为增加粮食产量,推广连作晚稻种植(把一年种一季的水稻改为种两季)。由于收割早稻、种植晚稻的时间挤在7月底8月初的十多天时间内,抢农时就是抢产量,人们把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合称为“双抢”。
顾名思义,“双抢”的艰辛不言而喻。金塘“农民诗人”徐吟兴在《双抢》一诗中说:“双抢”时逢三伏天,湿热交织到顶点。光秃田野无遮拦,淋漓汗水洒禾尖。
那时,“双抢”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和全家人的温饱。在没有农机的年代,“双抢”靠的是人工操作,拼的是全部劳动力,往往是全家总动员。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扯着嗓子叫我们起床去割稻。尽管总是睡不够又全身酸软,但还是硬着头皮一骨碌爬起。“沙沙沙……”挥舞着镰刀,一排排金灿灿的稻谷齐刷刷倒下。上午8点光景,割完一丘田,回家吃早饭。随后,大人们又马不停蹄地扛起打稻机、挑起箩筐往田里赶,我提着“挈档”(带甩的小水桶)到村头那口古井边打井水,“挈档”里配上舀水的竹管,水中倒点“十滴水”,放在田埂上供大家消暑解渴。
收割之后,就用打稻机脱粒。所谓打稻机,其实名不副实,确切的名称应在其前加上“人力”两字,即“人力打稻机”。因为打稻时得两个壮劳力一道配合使劲蹬打稻机的踏板,双手紧紧握着稻把一端往打稻机滚筒里伸缩,并不断翻动,黄澄澄的谷子顺着布满弓齿的滚筒滚落在稻桶里。装满一桶后,用簸箕把谷子畚出装入箩筐。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就咕噜咕噜喝两竹管井水下肚。半天下来,早已精疲力尽,还要把谷子挑回家。有时室外温度将近40℃,路面热得发烫,也得打着赤脚挑着50多公斤的谷子在上面行走。
14岁那年,我开始试着扛打稻机。或许打稻机的重量超出了稚嫩的肩膀可承受的范围,走着走着,我的脚一拐,瘦弱的身躯像青蛙那样扑倒在田埂上。父亲当时吓懵了,至今还记着这一跤。
“双抢”最怕遇到雷暴雨天气。有时中午刚刚放下饭碗,想眯一会儿,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全家赶紧出动,一路小跑赶到晒谷场,抢收早上挑出去晾晒的稻谷。
又闷又热又累,忙活了五六天,总算把早稻抢收完了,收割后的稻田经翻耕、平耙后,立即进行抢种晚稻。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赶到田头拔秧。一次,拔了一会儿,便觉得脚上痒痒的,用手一摸,摸到几条吸的鼓鼓的蚂蟥死死叮在小腿上吸血,令人毛骨悚然,吓得我哇哇大叫,用手反复拉扯,鲜血随即涌出。赶紧就地取材,用捆秧的稻草捆扎止血。后来大家配备了“蚂蟥竹管”,那手电筒搬粗的竹管内放置卤水或食盐,竹管的上口边钻个孔,串根麻绳,下田时随身佩带。下田后随时提脚观察,当发现蚂蟥叮在腿上时马上捉拿入管, 放工后将腌死的蚂蟥倒在野外石板上让烈日暴晒,因而夏季的乡间曲径不时能见“陈尸”的“蚂蟥干”。
“双抢”中的插秧也是重要的一环。插秧是个技术性强的手艺活,要做到行、株距适中,深浅适度,秧苗保持直立不倒,才能保证秧苗的成活率和水稻的生长,全凭谙熟的操作经验。面积大的田畈还要在稻田中间拉上几条细棕绳为作业道,借着这些棕绳,插秧者就可把稻行插直。
众人往往是一字儿排开,卷起裤腿,赤脚从田头开始,人站定,分腿,躬身,左手握着苗捆,右手食指和拇指飞快地从中分出三四根秧苗,捏紧苗身的根端,从左到右,用手指的力量将根须直接送进泥水里。株距则以双脚为界,左、中、右各两株,每行6株。插完一行,从田里拔出沾满泥水的腿脚,后退一步,紧接着是第二行、第三行,刚刚还是一汪泥水的田畈,逐渐有了满眼新绿。
“双抢”期间最快乐最惬意的时光当属收工后、晚饭前。此时大人、小孩会不约而同地汇聚于天然泳池“板桥头”附近的河里,在这里洗澡、消暑。一些调皮的孩子从古桥上纵身一跃,跳入水中,随即与同伴们打起水仗来。晚饭后,搬张竹床到屋外,与星光为伴,脑袋沾着枕头就睡着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记不清几岁就能摇头晃脑地背诵这首《悯农》,但真正对这首古诗有了深刻的理解,是在经历了“双抢”之后。